丁四新:中国古代的“和”:和谐大义及其观念展开

作者简介:丁四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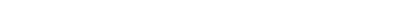
〔摘要〕“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观念。在和同说中,“和”是和谐、协调,“同”是蛌同、独断之义,中国古人普遍赞成“和”法,而反对“同”法。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婴“和其可否”和孔子“和而不同”最具代表性。在同异说中,“同”与“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有同的价值,“异”有异的价值;或同或异,都受制于“和”的原则,而以生生为基本指向。中和说起源于《礼记·中庸》,宋儒大力拓展了中和说。儒家的中和说以解决人的情感外发及其作用如何得当为关键。“太和”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指宇宙大和谐,另一种指政治大和谐。宇宙大和谐包括气论与性命论两种路数,而政治大和谐则包括人类、国家治理的大和谐及政治化的天人和谐。总之,“和谐”是宇宙生成、万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和生命存在的本原,是国家治理和规范社会、天人关系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和 和谐 同 异 太和 中和
“和”或“和谐”(harmony)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从宇宙到人生,从家庭到社会,从人际到国际,从政治到经济,“和”的价值和观念无处不在。“和”观念产生很早,它孕育于天人混沌不分的原始宗教意识中。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和”作为概念在西周晚期才正式提出。春秋末期,晏婴、老子和孔子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很重视“和”,将它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来对待。
《说文·口部》曰:“咊,相譍也。”“咊”或写作“和”,读去声,其本义指声音相应和。同书《龠部》曰:“龢,调也。”“龢”读平声,义为和谐、协调,经传多借“和”字为之。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和”,即是“龢”的通借字。作为哲学术语,“和”与“同”相对,前者指不同因素的和谐与统一,而后者则指单一因素的雷同和叠加。“和”与“异”也有差别,“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不同。本文以和同、同异、中和三对概念及太和、和谐两个概念为中心,来揭示中国传统“和”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观念的推展。
一、和 同
本节所说“和”“同”概念,是面对权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立场、态度和价值。求真、辨别是非和立身处世,是人类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基本内容。但是,如何求真?如何辨别是非?如何立身处世?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既涉及方法论也涉及价值观。在此语境中,“和”是和谐、协调,“同”是剸同、独断。中国古人普遍主张和赞成协调、和谐,而反对独断和剸同。史伯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子强调“和与同异”,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归纳起来,古人通常赞成“和”法,而反对“同”法。纵观中国古人的和同观,大抵可分为五种:第一种从事物生成的角度论和同,第二种从政治角度论和同,第三种从立身处世的角度论和同,第四种从求真辨理的角度论和同,第五种从做学问的角度论和同。
第一种从事物生成的角度论和同,阐明了古人辩论和同的意义所在,故此种论说具有总摄义。《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两句揭示了事物的生成原则是“和”而不是“同”。“和”是不同质料或物品的相互作用,而“同”则是同一质料或物品的叠加。五行的生成论哲学也是如此,史伯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是说,万物的生成是土行与其他四行相杂糅,而不是任何一行单独自加的结果。这说明了“和”是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制作羹食和弹奏琴瑟也是如此。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认为,做羹食,除了主料外,还需要配料、调料,以及“以火济水”的条件;而弹奏琴瑟则需要五声或多根丝弦的配合。这是“和”法。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很显然,晏子反对“同”法。史伯和晏婴所说的道理,在后世不断得到人们的阐发和引用。
第二种从政治的角度论和同,古人的相关论说大多聚焦于此。上引史伯说和晏婴说,本来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提问时阐述的。西周末年,周幽王昏乱,“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环侍其周围的人都是阿谀奉承、言听计从之徒,所以史伯据此断定西周殆将灭亡。晏婴说“和与同异”,是针对齐景公所云“唯据与我和夫”来说的。在晏子看来,梁丘据实际上是以“同”法来与齐景公交往的。从政治来看,所谓“和”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同”是:“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左传·昭公二十年》)。一般说来,可否相济的“和”法是人君决策正确和政治成功的保证。一言堂,一人独断,以及臣下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这往往是人主决策错误、政治失败的主观原因。西汉大儒刘向深化了晏子“水火相济”之说。关于水火如何相济,刘向说:“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说苑·杂言》)。刘向认识到了择人的重要性,“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说苑·杂言》),是君子掌权还是小人掌权,其结果是会迥然相异。东汉刘梁提出了“得由和兴,失由同起”(《后汉书·刘梁传》)的观点,对和同得失的关系作了简洁明快的概括。北宋彭汝砺做了更深入的议论,他说:“是非在理,不在同异。”将“理”作为判断是非的真实根据。应当说,彭汝砺的观点超越了此前诸种说法,因为同异毕竟只是权力现实化的表象,甚至或同或异,都有可能不过是权力外化的一种政治表演。
第三种从立身处世或修身的角度论和同,这种论说也很常见。《论语·子路》篇载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说“和而不同”从此即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虽然主张“和而不同”,但是他反对为和而和,更反对毫无道德底线的乡愿。《论语·阳货》篇载孔子曰:“乡原(愿),德之贼也。”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分析了乡愿何以是德之贼的原因:乡愿采取“同”法,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而成为“众皆悦之”的好好先生;但他以此“自以为是”,作出了坏的示范,所以说他妨害了人们在道德上的追求和进益。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提出了“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的观点,阐明了立身处世的德行本质是“仁”,由此深化了孔子“和而不同”的说法。东汉荀悦将“和”落实在具体的修身实践上,其法具体是:“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申鉴·杂言上》)。
第四种从求真辨理的角度论和同,此种论说在宋代以后颇为明显。除了上引彭汝砺“是非在理,不在同异”之说外,陆象山说:“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异字与同字为对,有同而后有异……此理所在,岂容不同?不同此理,则异端矣。”这段话表明,陆象山已完全超越了以往的和同之论,他不但认为“是非”高于“同异”,而且认为“理”是“是非”的判准,进一步深化了北宋彭汝砺的说法。
第五种从做学问的角度论和同,张载、苏轼、黄宗羲的相关说法比较突出。张载认为,学者之所以“乐己之同,恶己之异”,是因为他有固、必、意、我,不能做到虚心。苏轼批评了身居相位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另外,苏轼还对“同”作了反思,认为“同”应当“同于生物”,而不应当“同于所生”。重视生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价值观之一。黄宗羲认为,“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都是“一本万殊”的体现;他反对“以水济水”,认为抄袭和因循,都不是学问。黄宗羲重视学问的求真、求异和创新,而且认识到求异和创新是有密切关系的。
总之,“和”与“同”是基于求理和明辨是非的需要,人们在面对政治权威、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时所采取的两种态度和方法。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哲人赞成“和”法而反对“同”法。其中,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婴的“和其可否”和孔子的“和而不同”说法最具代表性。作为价值观念,“和而不同”还可以作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处理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中,“和”与“不同”都是必要的。
二、同 异
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变化不断,这是异。万物有联系,前后相贯通,这是同。同与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以存异,异以成同。客观世界的同与异,决定了主观世界的同与异。“同”有同的价值,“异”有异的价值。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复杂性。同异的主观辩证法来源于同异的客观辩证法。或同或异,从价值观上来看受制于“和”原则,而以和谐共生为基本指向。“求同存异”是一种寻求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大智慧。“求同”是指双方寻求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异”是指双方暂时搁置彼此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求同”和“存异”在此都是手段,其目的是双方的共生共存,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需要指出,“求同存异”中的“同”“异”概念,与“和而不同”中的“同”“异”概念是有区别的。从政治实践来看,前一命题主要是为了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交流、沟通与合作,而后一命题则通常是为了在同一关系体中实现上对下的宽容,便于下对上提出建议。后者在本质上是围绕权威应当如何表现及个人应当如何对待权威来展开的。
其一,古人从正面言及“同”的说法颇多,且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作为正面的价值原则,“同”所涉及的观点有三种。第一,“同人同心”之说。《同人》是《周易》第十三卦,“同人”是和同于人或与人和同的意思。《象传》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上乾下离,上天下火,天在上,火曰炎上,“与”是亲近之义,故《象传》曰“天与火,同人”。“类族辨物”,是说君子重视群体利益而轻视个人好恶。就《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易传·系辞上》引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嗅)如兰。”“同心”的说法是对“同人”的深化,这是说,二人只有做到了同心,才能做到同人。第二,“与民同乐”之说。孟子主张仁政王道之说,主张人君的个人欲望应当受到限制。在《梁惠王》等篇中,孟子基于义利之辨提出了“与民同乐”之说,而“与民同乐”的本质即是“与民共利”。同样的意思见于《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其中引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第三,《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说。“大同”说既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通过具体制度,大同社会展示了权力的公共性、道德的高尚性和天下利益的公共性。
作为正面的方法论原则,“同”所涉及的观点有五种。第一,“同”是同类事物相感相应、相与相求的前提。《乾卦·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说法,古人对人道人伦做了论证。第二,“同”是一种归类方法。《孟子·告子上》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第三,“同”是一种齐物方法。《庄子·德充符》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其中的“同”和“异”,都是作为观法来使用的。第四,“同”是一种与境界相关的方法,它也可以直接表示境界。《老子》第四章曰:“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同”是一种表示政治认同,或政治忠诚的方法和原则,这主要见于墨子的“尚同”说。
其二,由于世界是充满差异且不断生成变化的,因此“异”也是世界的本相,它应当得到肯定和尊重。理解世界、了解人情、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都应当尊重“异”,并由此去把握历史和现实变化的复杂性、差异性。关于“异”,中国古书的论述很多,可参看《管子·宙合》《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正论》《新语·思务》《淮南子·泛论》《礼记·王制》和《抱朴子·广譬》等篇。《管子·宙合》曰:“天不一时地一,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这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人类的职业和名位很多。《孟子·滕文公上》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齐”即异,即差殊之义,“不齐”是事物的实情或真相,治理国家即应当以“不齐”为基础,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事物的变化及其复杂性。就圣王之治,陆贾《新语·思务》说:“圣人因变而立功,由异而致太平。”陆贾从圣人立功和致太平的角度,强调了“变”“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三,虽然典籍有时强调“同”的重要性,有时又强调“异”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对于事实真相的反映,两者缺一不可。关于同异关系,中国古代典籍的观点和看法有四种。第一,同是整体,异是部分。《睽卦·象传》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上离下兑,上火下泽。火曰炎上,泽曰润下,故此卦有乖离、乖违之义。《象传》曰:“君子以同而异”,君子因此寻求大同而并存小异。大同和小异,分别是就睽卦的整体和上下两卦来说的;《睽卦》包含着求同存异的辩证思想。第二,异是特殊,同是一般。王充《论衡·自纪》曰:“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美色不同面”这是殊相,但它们皆是“美色”,“皆佳于目”,这是共相。前者是特殊,后者是一般。第三,异是手段,同是目的。《易传·系辞下》载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一致”是目的,“殊途”“百虑”是手段,没有手段之异,哪有目的之同?同和异在此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第四,异是表现同的境界。《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是说,孔子达到了与自然合一(“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和与历史合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天地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这是异;“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同。据此可知,异是对于同的人生境界的表现。
在当代,“求同存异”是一种实践智慧和政治智慧,它试图突破彼此的隔阂而实现双方交流、合作、共存、互赢和发展。“求同”是寻求双方可以沟通、合作、互利的共同点,而“存异”则是搁置双方的对立和争议。需要指出,这种智慧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根源,但是更多地它是一种被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所提倡和实践的大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国突破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对立及其利益冲突,而解决自身发展和生存矛盾的政治智慧。“求同存异”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为了自身的发展而走向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正向方法论。
三、中 和
“中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是“和”观念的演化。其实,“中”字产生很早,应早于“和”字。从甲骨文来看,殷人已产生了尚中的观念。据古文字学者的研究,“中”字本是一种带斿之旗,是用来测风向的工具。在《尚书·洪范》庶征畴中,“风”是五征中最重要的一征。在“中和”一词中,“中”是中正、不偏不倚之义。本节所说“中和”,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个专门观念。一般说来,“中和”作为一个观念,正式起源于《礼记·中庸》,中经汉人的解释,至宋代,儒者大肆推阐中和之义,提出了多种中和说。儒家的中和说,是在性命说的理论背景下着重解决人的情感外发及其作用如何得当的问题。刘向、程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有中和说。
先看《礼记·中庸》本文的相关说法。《中庸》的中和说有两种,一种属于本体论,另一种属于实践论。前一种是儒家中和说的主流。《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很明显,“中”“和”两个概念均是就喜怒哀乐的情感来说的,“中”就未发言之,而“和”就已发言之。“中”兼具“内”与“不偏不倚”两义。“中”是大本,“和”是达道,“致中和”是工夫及其所至境界。郑玄注曰:“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郑玄将“中”所含的情感作为礼乐、政教之本,这是比较符合先秦儒学传统的。《中庸》又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段话将“中和”作为道德实践的尺度或原则。
再看汉人的中和说。中和、中正,是汉代流行的核心价值。以中和为养生的基本原则或作为材性品第的标准,这是汉人的通义。而这一点,其实与汉代流行的气化论哲学颇有关系。《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法言·先知》《论衡·率性》《申鉴·政体》《人物志·九征》《老子河上公章句·无为》等均有相关说法。《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人物志·九征》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刘向的中和说则比较不同,《论衡·本性》篇引刘向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未发谓之阴,已发谓之阳,此种思路受到了《中庸》未发已发说及汉人阴阳观念的双重影响。刘向中和说与宋儒的中和说比较接近,前者开了后者的先河。
又看理学的中和说。理学的中和说以程颐和朱熹的说法最为重要。《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曰:“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这段对话辩论中和,属于工夫论进路。有人询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的问题,程子回答说,求中必用思,而思即是已发,故于未发之前求中,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程子认为,未发之前的工夫应当是涵养,而不是思求。朱子《中庸章句》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朱子以性情论解释了《中庸》的未发已发说,正式建立了理学中和说的基本解释框架。
最后看心学的中和说。心学的中和说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王阳明说:“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王阳明从工夫角度对何谓中、何谓和作了定义,并认为中和工夫有高低久暂之别,惟天下之至诚“能立天下之大本”。在《答董吴仲论学书》中,黄宗羲总结和批评了三种宋明儒的“致中和”主张,他继承刘宗周的观点,认为“致中和”的工夫在于“诚意”;而“意为心之所存”,是心的本体,而不是作为心之所发者。
总之,中和是古人所推崇的重要价值观念和方法论。从先秦至两汉,中和主要作为价值观念来使用。但从宋代开始,新儒学沿着《中庸》情感之未发已发思路将中和说推进为一种在思想上不断发展、深化的工夫论。中和工夫论是宋明儒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
四、太 和
“太和”,义为极其和谐。大约说来,“太和”在古书中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宇宙大和谐,另一种是指政治大和谐。这两种用法相混合,产生了“太平气”这样的词汇。宇宙大和谐包括气论与性命论两种路数,而政治大和谐则包括人类、国家治理的大和谐及政治化的天人和谐,且此种“太和”具有境界义。“太和”一词产生于先秦,汉代“太和”“太平”观念很流行,宋代以后张载等人用“太和”来描述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
先看性命论的“太和”说。《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一词最先见于本段引文。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性命论兴起。性命论是天命论的下落、转进和内在化。“乾道”即天道,天道是性命的本原,“变化”即生化。“保合太和”是就气化流行来说的,指万物各自保合禀受其在自己的太和之气,如此则性命不失。在这段引文中,“太和”有两义,一指在物内的冲和之气,一指极其和谐的社会存在状态,《乾卦·彖传》曰“万国咸宁”,即演绎此义。
与性命论的太和说相关,古人认为和气或太和之气流行于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本原。养生即是保持此和气,体气有沴则病伤,和气丧失则死亡。《礼记·郊特牲》曰:“阴阳和而万物得。”《论衡·气寿》曰:“圣人禀和气,故年命得正数。气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同书《订鬼》曰:“气和者养生,不和者伤害。”《老子河上公章句》曰:“‘人之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也。‘其死也坚强’,人死和气竭,精神亡,故坚强也。‘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气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气去也。”朱子曰:“人皆自和气中生。天地生人物,须是和气方生。要生这人,便是气和,然后能生。人自和气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这些引文都说明了,道家和儒家都以“和气”为生命的本原,具有宇宙生成论的意义。
再看气论的太和说。气论意义上的“太和”概念是从“和气”提升起来的。“和气”概念出自《老子》。《老子》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或“和气”是万物当下存在的本原。随后,“和气”上升为宇宙论概念,宇宙和谐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流行。《淮南子·泛论》曰:“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淮南子》这段话极具概括性,“和”是宇宙生化流行的应然法则,“和之精”指太和精气,万物得此太和精气即以生以成。王符在《潜夫论》中更直接地提出了“和气生人”的命题。严遵提出了天地万物生成的四因说,《老子指归·上德不德篇》曰:“道为之元,德为之始,神明为宗,太和为祖”,其中的“太和”即指太和之气,是万物的生成本原。在《正蒙·太和篇》中,北宋哲学家张载进一步提升了“太和”的定位,“太和”或太和之气即为宇宙生化的本原。
最后是作为政治大和谐的“太和”概念。政治大和谐的观念起源很早,《尚书·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乾卦·彖传》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协和万邦”与“万国咸宁”同义,都是指政治大和谐、天下太平。“太和”和“太平”也具有政治境界义,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太和”或“太平”可以单纯指国家、社会治理所达到的大和谐理想境界,而且在更多时候,它们置身于天人关系或天人感应的思想背景中。《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应”是宇宙之理,“感通”是“感应”的一种形式。圣人的感通与天下和平有因果关系,汉代的太和说或太平说,常常带有神性的天人感应特征,如公孙弘在《举贤良文学对策》中说:“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汉书·公孙弘传》)这段话很经典,它首先认为“感应”是宇宙之理,其次按照心和→气和→形和→声和→天地之和列出了前感后应之序,再次具体描述了天地之和的瑞应,而瑞应表示“和之至”和“和之极”。从人感天应及休征祥瑞并现来看,此天是神性的天。公孙弘所描述的“和之至”及“和之极”的境界当然属于太平或太和的政治境界。这种人大其心而能感通天地,乃至达到太和状态,在宋儒周敦颐《通书·乐中》“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中也能读到。
五、和 谐
“和”或“和谐”,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核心价值,它贯通于自然、社会、人生、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之中。而围绕“和”,中国古代哲人和各界精英都作了大量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命题。上述各节所述古人对于和同、同异关系的比较和议论,对于中和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太和说的阐述,都无疑是围绕“和”这一关键概念展开的。综合起来看,古人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和”或和谐,是宇宙生成和天地万物存在的必要条件。《老子》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从道生论出发,认为阴阳和气是万物生成及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乾卦·彖传》从性命论出发,认为性命与形体“保合太和”,才有利于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不仅如此,在先秦时期,古人已认为“和谐”是内在于自然事物而使之生成的特性。在“和”的基础上,古人进一步提出了“太和”的概念,“太和”即极其和谐之义。严遵及汉末《太平经》都将“太和”肯定为宇宙法则,天地万物的生成都必须依赖于此法则,并将其看作万物生成的本原之一。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太和说继承了此种思想。《吕氏春秋·大乐》曰:“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段话是说,万物的形体在现实中落实下来没有不发出声音的,而声音出自和谐,和谐出自适宜,和谐与适宜是先王制定音乐的两个基本原则。从这段话来看,不仅和谐、适宜是先于制乐而存在,是客观的法则,而且追本溯源,它们都出自终极始源——“太一”。
其二,“和”或和谐,是生命存在的本原。得“和”即意味着生存,失“和”即意味着死亡。《管子·内业》曰:“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这段话说得很直白,“和”指精气与形体的和合、和谐。生命的和谐有两层,一种是体气或肉体的自然和谐(生理和谐),一种是心理的和谐,包括精神与肉体的和谐。从养生看,后者更重要。通行本《老子》第五十五章曰:“(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嚘),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两句,简帛本作“和曰常,知和曰明”,当从简帛本。这段话认为,“和”或“知和”是养生的关键,养生应当自然,既不能用益生之法也不能用“心使气”之法来养生。身体和谐、体气精和、心理和平、行为适中,这是养生延年、身体健康的基本方法和观念。相关文献可参看《国语·周语下》《吕氏春秋·适音》《难经·藏府配像》等。而《庄子·天道》所说“人乐”“天乐”的生命境界,也以“与人和”和“与天和”为基础。
其三,“和”或和谐,是贯穿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政治原则。郭店简《尊德义》曰:“善者民必富,富未必和。不和不安,不安不乐。”达到“和”或和谐,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是使民和,构建和谐社会,而“和”是人民幸福快乐的前提。从工具看,儒家主张以乐和民。《诗经·商颂·那》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小雅·鹿鸣》曰:“鼓瑟鼓琴,和乐且湛。”从德行看,儒家其实主张以德以仁和民。《左传·隐公四年》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同书《僖公五年》曰:“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队要打胜仗,内部团结是很重要的。《左传·桓公十一年》曰“克在和,不在众”,《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认为“人和”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关键条件。
其四,“和”或和谐,是处理义利关系的一个高级原则。社会是否公平正义,这需要用“和”来处理义利关系。国家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和谐幸福,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国家和社会的总体经济状态及其财富分配。纯粹从逻辑的立场来看,义是利益获得的绝对准则,或者说所有利益的获得都应当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礼记·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这种“义”至上主义利益获得、享有和分配的观念。但此种观念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会忽视甚至挤压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进一步影响社会稳定和削弱国家统治的基础。因此,孔孟等儒家以“仁”观念来补救之。“仁”在人文层面是讲求人本,在心理层面是讲求恻隐,在经济层面是讲求施惠让利,与民共利。《乾卦·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利者,义之和也”是对于“元亨利贞”之“利”字的解释,“物”在此指人民,“利物”即利顺于人民。“利物足以和义”即是说,利顺于人民,即足以和合于义。或者说,和于义,即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享有是否有利于人民,是否顺遂于民心。实际上,社会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稳定,其基础即在于利益如何分配和享有。《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寡”即“贫”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曰:“王何必曰利”,这都是重视“利”的社会性和人民性。总之,《乾卦·文言》将利益的正当获得与享有,转化为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共享,并以“和”来处理此一问题。
其五,“和”或和谐,是国家、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人民是否快乐的道德准则。儒家和墨家等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儒家的意识更强烈。一般说来,家庭、社群、国家和天下的存在都需要和谐团结的局面作为其基础,而如何做到和谐,这不仅是利益诉求的问题,而且涉及伦理秩序和道德教养问题。儒家以仁义为德行规范,以礼乐为手段。《论语·学而》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宋儒朱子以“吾心安处便是和”诠释了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云:“礼如此之严,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处有个和?须知道吾心安处便是和。如‘入公门,鞠躬如也’,须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见得礼中本来有个和,不是外面物事也。”朱子在此深入到道德心理层面来解释社会和谐问题。而宋明儒学之所以特别强调工夫论,这是有原因的。竹书《五行》是子思子的著作,它是一篇论述内在道德修养及其身心和谐问题的专文,提出了“慎独”“为一”的工夫及“为善”“为德”的道德境界。“慎独”是舍弃德之行的五行而专门谨慎其内心(“舍夫五而慎其心”),“为一”则是通过“慎独”工夫而使此德之行的五行和谐为一(“以夫五为一”)。“慎独”“为一”是“为德”工夫,而“为德”是“慎独”“为一”的境界。“为德”的境界,是指德之行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达到和谐如一的状态,竹书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为善”的境界,是指德之行的仁义礼智四行达到和同的状态,竹书曰“四行和谓之善”。孟子说人性善及其修养,即着重继承和发挥了《五行》“四行和谓之善”的说法。
其六,“和”或和谐,是定义天人关系的应然法则。天人和谐包括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本然和谐和责任意识上的应然和谐。在中国古代,天人和谐通常表现为天人感应和天人感通两种形式。感应本是彼此联系和作用的两个主体的基本特性,具有普遍性。但是,在神化或人格化的自然观中,感应往往以人感天应的形式出现,且垄断神权的人君是“感”的一方。天人感通是天人感应的深化版,发源于《系辞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宋代开始流行。天人感通说大大增加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的意志力量和主体能力。它认为,通过工夫实践,人的意志、良心和能力可以感动并打通“天”的一方,让“天”按照人的意志产生回应。当然,宋儒所说的“天”基本上已经被客观化了,不具备神性特征,他们认为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之良能。宋儒极力强调工夫论的重要性,这与天人感通说是一致的。而在无神论流行的当代中国,天人和谐已经转变为人与自然(nature)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和”或“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当今世界来看,“和”具有普世性。文明的存续、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共生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都离不开“和谐”原则。而“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两大主张无疑都体现了“和”的精神和价值。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1期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