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近年来,中国美食正日渐成为人们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广受欢迎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详尽地展现了中国各地美食的制作经过;最近的《风味人间》纪录片更跨出国门,寻味足迹遍布全球5大洲20多个国家,用特写镜头和家庭故事记录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准备美食与品尝美食的盛景。纪录片中不乏对中国美食博大精深的感慨,比如《风味人间》在一开头就赞美中国美食丰富多样、饱含智慧和温情,中国,拥有最富戏剧性的环境和气候,从荒漠到平原,从山地到海洋,人们因循自然,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
在观看这些展现中国美食文化、美食奇观纪录片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批评。比如去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出版的、英国写作者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的《鱼翅与花椒》,就以外来者的角度,写到了中国人对吃无所禁忌、日常烹饪充满残酷。
或许我们不应该把扶霞的看法视为来自其他文化的偏见,因为作家阿来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也曾表示,他不想将自己的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涉及的内亚边疆上的高山物产虫草、蘑菇(松茸)和岷江柏,写成美味的舌尖上的系列,我们为何会是一个吃货的国度,在畸形的消费社会里沉溺于感官欲望?阿来问道。
杂食中国人:啥都吃与烹饪的残酷
《鱼翅与花椒》一书序言的标题是中国人啥都吃。啥都吃,这是外国人自古以来对中国美食根深蒂固的印象。扶霞在书中提到,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记录了中国人吃猫肉、老鼠以及动物生殖器等奇闻;甚至到了21世纪,英国媒体还会公开抨击中国菜,说中国的食物具有欺骗性,永远不辨真实面目。作为一部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非虚构作品,这篇以中国人啥都吃为标题的序言,看起来并不怎么诱人,反而诚实地道出了外国人初体验中国食物时的恶心与惊奇。她在香港的一家餐厅第一次品尝皮蛋,这个陌生的食物长得很恶心,咬到嘴中也有股恶臭,根本无法下咽。
中国人啥都吃并非扶霞一人之见,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记者、饮食作家林留清怡也记录了她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最初印象。在中国吃饭,林留清怡的身份远比扶霞有利,她是华裔美国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很多人都把她当成本土中国人,然而,要真正接受中国菜,她也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她发现,在中国餐馆点菜犹如探雷——菜单上的名字并不能透露出这些食物究竟是内脏、爪子还是舌头。为了更加熟悉中国的饮食圈子,她也入乡随俗地尝试了狗肉和动物鞭器。她去过一家专业的鞭餐馆,并在一位营养专家的伴随指导下尝试了牛鞭、多种鞭熬制的汤,甚至还咬了一口羊睾丸。这个行为随后被营养专家叫停,她告诉林留清怡,羊睾丸这东西只有男人能吃,女人吃了会长胡子。吃菜也分性别,这是她在鞭餐馆学到的混杂着中医学的营养知识。之后在北京的烹饪学校,她学到了更多千奇百怪的中餐知识,比如吃鱼头可以修复脑细胞、吃辣气色好、美国人胖是因为吃面包。

扶霞将中国人啥都吃总结为杂食性。杂食性的特征不仅指中国人食材的多种多样、缺少禁忌——用她的话说就是,中国人不会把动物分成宠物和可以吃的;还包括了中国烹饪过程的残酷性:菜场里人们冷漠且放松地屠宰动物,饭桌上,同桌的中国朋友充满热情愉快兴奋地期待活蒸虾,同样令她感到不适。此外,啥都吃也是一种由中西饮食口感审美差异造成的误解,中国美食中欣赏的口感,比如软韧、滑腻、爽脆、黏腻的英文对应词,都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
虽然扶霞和林留清怡已不再像她们的前辈一样,没有根据地指责中国人杂食的荒蛮(扶霞明确地写道,某些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人是因为饥饿才去吃鸭舌头和虫子实在是出于无知),但她们也确实在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同时,再一次强化了中国饮食杂食与残酷的特色。她们将自己深入熟悉中国美食的经历称为冒险,扶霞将自己对某些中国菜(比如脑花)的初体验,形容成狂野甚至毛骨悚然的,林留清怡也将味觉形容为混乱而强烈的。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们的口味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残酷,扶霞说,中国让她成为了一个杂食动物,也让她习惯了在菜场观看动物被宰杀的过程。因为,在她看来,与外国人的少见多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对自己啥都吃这件事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需要追问的是,对于啥都吃或烹饪的残酷,中国人真的保持了沉默吗?确实,一些中国作者是认可中国人啥都吃的,比如美食家汪朗就在《食之白话》里充满自豪地写道,中国人研究吃之深入,敢称天下第一:因为中国人吃得全面,甚至包括蚂蚁蛇蝎,而且吃得彻底,从主体到细节全部囊括。(汪朗略显嘲弄地提到西方人对狗肉的禁忌,他把狗肉当作牛肉招待外宾,外宾觉得好吃,后来还主动要求再来一盘和上次一样的牛肉。)——基本印证了扶霞的观察。
也有人对啥都吃这一点存疑。在《老饕漫笔》里,饱尝中国美食的掌故家赵珩也写到了啥都吃的广东美食,明显带着惊讶的情绪。赵珩说,吃蛇、吃猫、吃猴子已经令人咋舌,而吃龙虱、禾虫,北方人听听也觉得恶心。他还写到,中国文人讲究君子远庖厨的传统,其原因不仅在于将厨事看做是贱役,更在于回避屠宰动物的残酷场面,不忍见血淋淋的肢解牲畜的景象。赵珩将特别残忍的吃食方法——类似活吃猴脑、活猪取肝等——称为残忍陋习,认为它们并不属于饮食文明。赵珩对于啥都吃的惊讶,以及残忍吃食的敏感,就与扶霞的结论正好完全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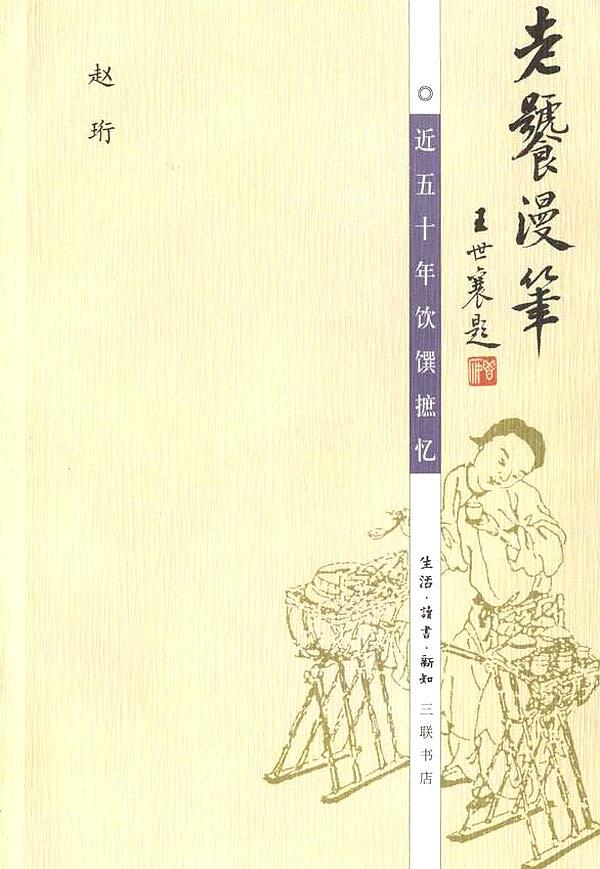
是落后还是艺术:中国人太沉溺于吃了吗?
汪朗说,中国人热爱钻研吃。扶霞和林留清怡都以饮食为媒介结交了一些中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见识到了中国人对于吃的热情。扶霞的一位朋友热爱钻研美食,扶霞评价说他对吃的钻研和热情,可与宋朝的苏轼相提并论——苏轼在遭遇数次贬谪之后才开始躬耕陇亩、洗手烹鲜,这位朋友遭遇家庭变故之后,最终在厨房的色香味中找到了乐趣和自由。林留清怡在烹饪学校结识了一位烹饪老师,她被邀请进入了烹饪老师的家庭学习做菜,也邀请烹饪老师来到她家包饺子。随着她们聚在一起烧菜次数越来越多,烹饪老师对她透露的自家故事也越来越完整,准备饭菜成为了彼此交心的时间,这项传统的家务劳动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打破了我们师生之间的藩篱。烹饪老师曾讲到饥荒时代自家四个孩子分食一个苹果的故事,老四得到了大半,老二得到了小半,老大得到了苹果皮,而老三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来讲的,然而在这位美国学生听来却觉得异常辛酸。
来自海外的写作者们,一方面赞许中国人对吃怀有毫无功利心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觉得中国人有沉溺于吃的嫌疑。扶霞饶有意味地将中国人对吃的迷恋与工业与科学的落后联系在了一起。她写道,中国人对自己美食文化的骄傲中藏有怯懦,也许隐藏在这自豪之后的意识是,中国的享乐主义和普遍的自我放纵可能是中国比起现代西方国家有些落后的原因。她似乎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中国人看到活生生的大小动物,不是选择吃了它们,而是坐下来耐心地观察思考,它们会不会在生物学上有更大的进步呢?要是它们不那么醉心于炒锅里的化学反应,是不是就能产生更多杰出的化学家呢?她进一步将自己丝毫不讲究美食享受的祖国英国与中国进行了对比,也许正是英国人那些糟糕的暗黑料理,再加上冷水澡与冷漠的感情,才让他们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要是中国人不是这么忙着吃来吃去,也许就能更早开始工业化,赶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先把这群西方蛮子给殖民了。

扶霞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检视,不光在中西发展落差这一类宏观的尺度上,在微观层面上,她也观察到了中国饮食中可能存在的不卫生与科学落后。她的朋友给了她一些看上去很可疑的食物,她也渐渐爱上了一些以前想也不曾想的零食。比如火车站售卖的火腿肠,她很清楚它的原料,人工再造的猪肉,加上一些谷物淀粉,用红红的塑料皮套套起来;还有粉红色的带状泡泡糖,她很喜欢吃这种泡泡糖,以至于生了多颗龋齿。
人工味精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中餐对味精的广泛使用,在排斥味精的西方世界看来,是不健康甚至有害的,味精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餐的国际声誉。扶霞认为,味精的广受欢迎和它在中国推广的年代有关,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仍非常艰难,味精高汤不用加肉也能生鲜;味精依赖也与中国人对科技的乐观态度有关,中国人才刚刚摆脱了饥荒,饥荒的记忆还未远去,旱涝灾害也时时威胁着农业的收成,所以人们普遍相信科技会带来好处,而西方明显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
林留清怡也同样注意到了中餐味精的问题,与扶霞在厨师学校观察思考不同,她专程跑去了河南莲花味精厂现场勘查味精生产环境,也由此厘清了味精到底有什么危害。参观完味精厂,她吃了一顿放了不少味精的饭菜,之后除了口渴并没有什么别的异常反应。经过调查,她发现,美国的食品添加剂其实也有很多,单单只有味精深受诟病,而且,不光中餐广泛使用味精,美国的许多食品也加入了味精。正当林留清怡觉得自己改变了对味精的成见时,她又发现了味精厂对当地环境的污染,但当地人并不承认。她写道,想向人们说服味精厂对环境有污染,就像说服美国人味精对人体无害一样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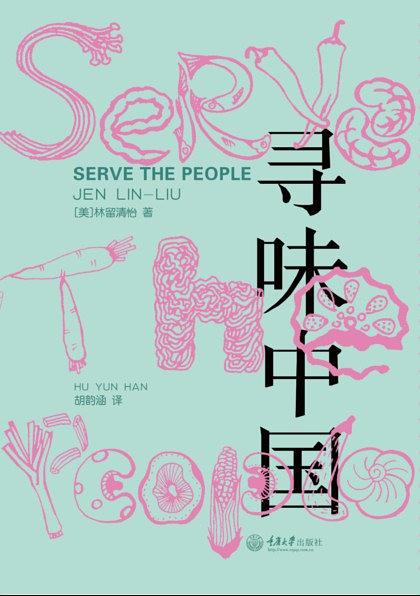
扶霞认为中西方饮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仅是可疑的中国食物添加剂就能证明这一点,与之相对的,已故的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逯耀东在美食散文集《肚大能容》中也提出,中西饮食属于不同的类型,但他的结论并非中国饮食更不科学,而是更加艺术。他认为,正如中西文化不同,中国吃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在林留清怡那里,这种艺术性可能体现为烹饪老师对于包饺子加多少料总是含糊其辞),食谱与琴棋书画同在四库总目的一类当中;而在美国吃是科学的,讲究的是标准和卫生,例如美国家庭厨房就是现代科学产品的展示。不过,逯耀东认为,可惜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人吃的艺术正逐渐被美国的吃所同化或取代,传统风味的吃食也越来越少。
吃的内涵:饥饿记忆与家庭温情
在部分外来观察者的眼中,中国人对吃的热情可能与饥荒的记忆有关。在苏童的小说《白雪猪头》里,猪头更是成为了食物不那么充裕时代的家庭温情的象征。小说从母亲买不到猪头肉的困境写起。母亲凌晨就去肉铺排队,可是怎么都买不到猪头肉,她明明看见肉联厂送来了8只猪头,4只大的,4只小的,可是只放出来了4只小猪头,另外4只被别人套关系预订走了。小说是这样写母亲看到邻居家猪头的艳羡之情的,我母亲的一只手突然控制不住地伸了出去,捏了捏猪的两片肥大的耳朵。她叹了口气,说,好,好,多大的一只大猪头啊!母亲并不是自己馋,而是家里孩子多,要吃肉。母亲决定利用自己的缝纫特长,为肉铺员工的小孩做衣服,以此来争取肉铺的猪头。做衣服的时候,她却唉声叹气,因为肉铺员工小孩的腿一个比一个长,给的布料根本不够用,她想,一定是骨头汤喝多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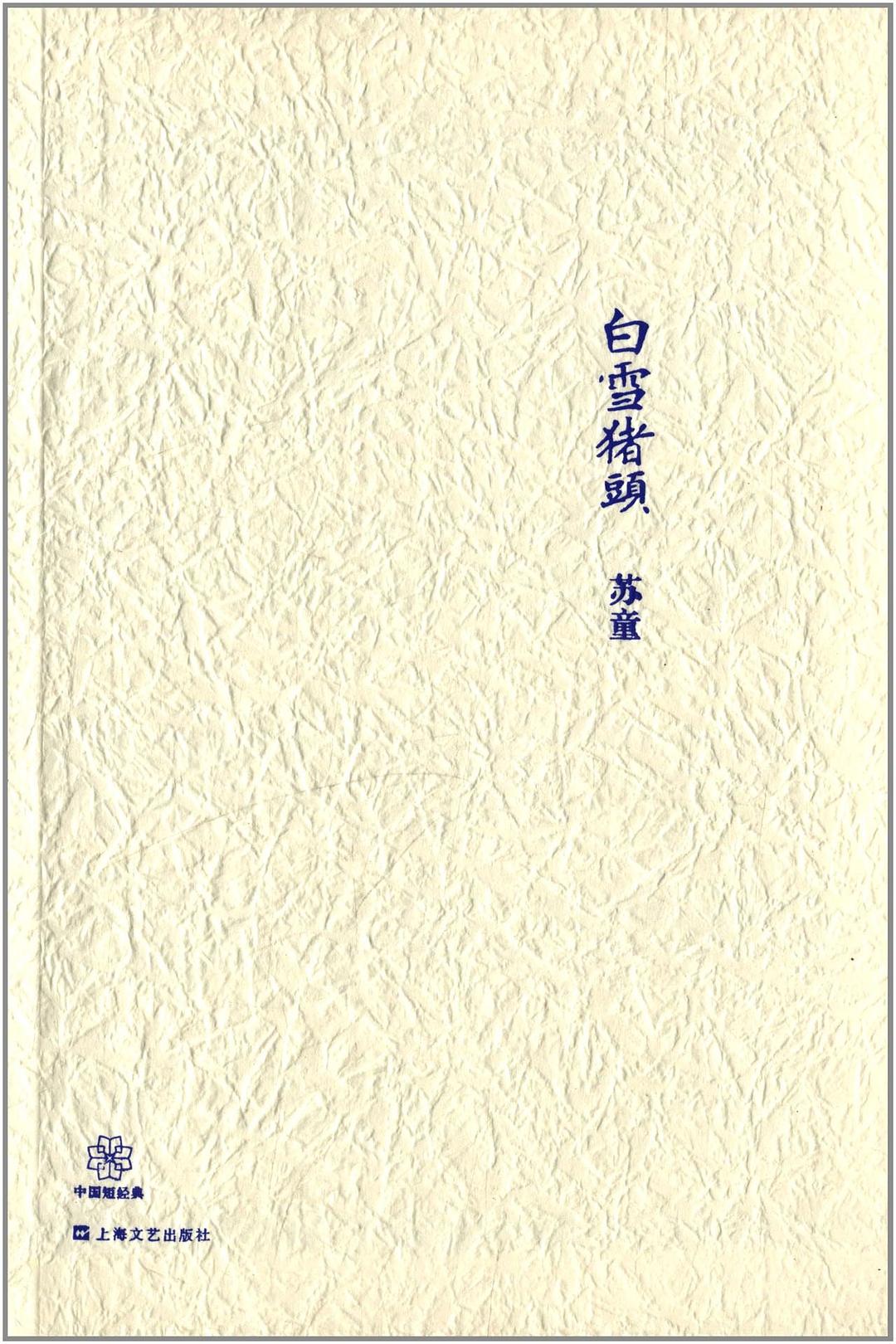
汪朗在《食之白话》里写,猪头不怎么受人待见,最初是穷人的吃食,大户人家是不屑与猪头为伍的。然而苏童笔下的这家人却将猪头看作是极其珍贵的美食,孩子们最终在雪地里看到了别人送来的猪头,那场景如同显圣的奇迹,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左手一只,右手一只,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两只大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也覆盖着白雪,看上去风尘仆仆。对于正成长的孩子来说,猪头不仅满足了食欲,还象征着母亲和家庭的温情。
值得一提的是,美食与家庭温情密不可分,这也是近年来的美食纪录片着力刻画的内容,从《舌尖上的中国》到《风味人间》,我们从中频繁看到阖家团圆、共享美食的场面。在《新京报》对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的采访中,他也一再表达了对于家庭美食的怀念,尽管这些美食看起来和苏童笔下的猪头一样朴素,在难受的时候,最想吃的只是妈妈做的白粥和咸菜,他最爱的也是家乡味道,蒸的水烙馍,放上鸡蛋和蒜米;用鸡骨架或者羊骨熬的面糊汤,打上鸡蛋,加点胡椒。

《白雪猪头》讲述的是饥饿年代里家人挨饿、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而陆文夫的《美食家》则更接近逯耀东所说的逝去的饮馔艺术,这种美食艺术与充分承认、尊重人的食欲有关。《美食家》讲述的是平民出身、投身革命的我与讲究吃喝之道的美食家之间,从旧社会一直到新时期的口味之争。美食家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去苏州的朱鸿兴吃一碗面,他不光对面的硬度、汤料、蒜叶有讲究,对面汤是不是头汤也有讲究;而我出身贫苦,为了给家里挣点饭钱,不得不受他差遣帮他跑腿。建国后,我接手了苏州有名的餐馆,在反对奢侈享受的思想指导下,把菜单上那些精细讲究的菜肴,比如松鼠鳜鱼、蟹粉菜心,毅然替换成了大众喜欢的白菜炒肉、大蒜炒猪肝。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大众来是来了,却不怎么喜欢更新的饭菜,因为他们还是更喜欢虾仁,而不是白菜。
在之后的大跃进和困难年期间,我和美食家都饥饿难耐,美食家来借我家的南瓜充饥,还跟我画饼充饥般聊起了吃。美食家说,因为这些时日没什么吃喝,夜里睡不着,就想起这辈子吃过的好东西。他在吃的方面记忆特别好,可以记得起几十年前吃过的名菜,在什么地方吃的,是谁烧的,入口什么样,余味又是什么样,即使是南瓜也可以做出上等的口味,接着即兴创造了南瓜盅的食谱,把八宝饭放到南瓜里回蒸……
进入新时代之后,美食家凭借对菜肴口味的出色记忆和分析,再一次被邀请到饭店传授美食知识。他讲起苏州菜的风味,除了甜还有盐,盐能吊百味,百味吊出隐而不见。人们佩服他,问他这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他说,这门学问一不能靠师承,二不能靠书本,全凭多年的积累。人们于是尊称他为美食家。人人都吃,却有人食而不知味,美食家能够将其中的奥秘道出,在经历了饥饿时代的人们看来,这个美食家已经不再是贪图享乐的代称,而近乎成为了解人性、尊重人性的专家。听了美食家讲授美食,有人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建立在了满足食欲、尤其是满足美食欲之上,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大家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菜!
中国人热爱吃,谈论吃,不仅仅是出于饥饿的记忆,而是因为,吃,一方面联结着昔日家庭温情,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正在消逝的饮馔艺术。然而,在人们普遍远离故土、漂泊在外的今日,也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美食是否如同许多美食家所言那般,注定出自家庭制作、最好是不可复制的本地风味?相比之下,远离地道乡土的、批量制作的外卖餐食,是否就不值一提呢?这个问题,或许比怀念昔日家庭温情与饮馔艺术更有意义。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
本文经用户投稿或网站收集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
